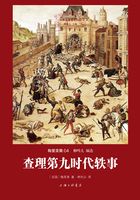
第5章 年轻的廷臣
阿埃基摩:戒指已经赢过来了。
波塞摩斯:石头是牢不可破的。
阿埃基摩:不见得,因为您的老婆是那样易于接近。
莎士比亚《辛白林》
到了巴黎,麦尔基希望能够有人大力地把他推荐给海军上将柯里尼;据说有一支军队将在这位名将指挥之下开往弗兰德尔作战,他希望到这支军队中服役。他带了几封信投见他父亲的几个朋友,他妄想他们会支持他的计划,举荐他到查理的朝廷里和海军上将跟前——海军上将也有他自己的一种朝廷哩,麦尔基知道他的哥哥很有一点信誉,然而他该不该再去找他,自己还很犹豫。乔治·德·麦尔基脱离宗教,使他自己完全跟他的家庭分开,他在他家里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了。这并不是一个家庭被宗教论点的不同弄得不团结的唯一例子。很久以来,乔治的父亲禁止当他在场的时候说出“背教”这个名词,而且引用了《福音书》里说的“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它”来支持他的这种严峻的观点。虽然年轻的柏尔那尔并不同情这种不屈的意志,可是他哥哥的变化在他看来,毕竟是他家庭的荣誉上一道可耻的痕迹,而且兄弟间的友爱必然会因这种意见而大受影响。
在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该怎样对待他以前,甚至在没有把他带来的荐函投递以前,他认为得尽先想想办法去充实他那只空洞洞的钱包,因此他便走出小旅馆,上圣·密薛尔桥上一个制造金银器皿的商人家里——这人欠了他家一笔钱,他是受托来催讨的。
在桥头,他遇到了几个打扮得很文雅的青年,他们臂挽着臂站着,差不多完全挡住桥上那条狭窄的过道——那是桥两边无数的店铺和货摊中间给留下的过道,这些店铺和货摊就像是两堵平行的墙壁耸立着,完全挡住行人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河水。在这些先生后面,走着他们的仆人们,手上都拿了一把套在鞘里的叫作“决斗”的双锋长剑和一把腰刀,腰刀的外壳是那么宽大,必要时可以当作盾牌来用。毫无疑义,这些武器的重量对于这些年轻绅士是过于沉重了,或者他们很得意显示给大家看看,他们有的是打扮富丽的仆人。
他们似乎都很高兴,这至少可以从他们那连续不断的哄笑声推断出来。假如有一个打扮不错的女人从他们跟前走过,他们便露出又像客气又像无礼的混合表情向她致敬;这些轻佻青年,其中有好多个居然用肘粗暴地碰几个身穿黑色大衣道貌岸然的上流人,这些人只好闪避开,口里极小声地咕哝出成千句的诅咒,骂那些廷臣的侮慢举动。那一群青年中,只有一个人低着头走路,好像一点儿没有参与他们的作乐行为。
这些青年中有一个拍拍他的肩膀嚷道:“真见鬼!乔治,你的脾气变得非常忧郁;已经一刻多钟你没有开口了。难道你有意做个苦行僧吗?”
“乔治”这名字使麦尔基听了浑身发抖,但是他并没有听见那个被称呼这名字的人答话。
“我用一百个比斯托尔[35]跟你打赌,”先前那个人接下说,“他还在恋爱着那一个难对付的女人,可怜的朋友!我同情你;在巴黎碰到一个残忍的女性,那是要倒霉的。”
“上魔术家律贝克家里去吧,”另一个讲,“他会给你一种媚药,使你能在情场中得意。”
“或许,”第三个说,“或许我们友好的营长爱上了一个修女吧。这些胡格诺魔鬼,不管改变了信仰没有,总是不放过身许上帝的那些女人的。”
麦尔基立刻听出一个熟识声音忧悒地回答:
“咳!假如单单是关于一时的爱情,我哪会这样发愁呢;但是,”他更低声地再说下去,“那个受我委托带封信给我父亲的德·蓬回来了,他告诉我说,我父亲坚持不再愿意听旁人谈起我。”
“你父亲是老派人,”一个青年说,“他是那班企图取得安布亚兹宫的那些老胡格诺中的一个人呀。”
这时候,乔治营长无意中转一转头,看到了麦尔基,发出一阵惊奇的叫声,他张开着两臂向他跟前奔去。麦尔基一点儿也不踌躇,便向他伸出了手臂,把他紧紧地抱到自己的怀里。假如他们的会见不是如此出乎意料的话,那么他或许会试试用“无动于衷”的心理来武装自己;可是惊诧的情绪使本性恢复了它的一切权利。从此刻起,他们便像朋友们在一次长途旅行之后久别重逢似的相视了。
在拥抱和初步地盘问些情形之后,乔治营长转身向他的朋友们,他们中间有几个停下来在仔细地打量这个场面。
“诸位先生,”他说,“你们看到这次意想不到的遇见了吧。请原谅我,我要离开你们去跟我七年多以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兄弟谈谈。”
“不成!我们不同意你今天离开我们。晚餐已经吩咐过了,你一定要在场。”说这些话的人同时拉着他的大衣不肯放。
“贝维尔说得对,”另一个说,“我们决不让你走。”
“唉,这有什么!”贝维尔又说,“希望你弟弟也来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我们多了一个好伴侣就是了。”
“对不起,”麦尔基于是说,“我今天有许多事要办。我有几封信要投交……”
“你可以等到明天再投呀。”
“那些信必须今天投交……而且……”麦尔基带着微笑并且有些不好意思地又说,“我索性坦白告诉你们吧,我身边没有钱,得去筹划筹划。”
“呀!真的,好借口!”他们同时都嚷了起来,“我们不能够容许您,为了要去向犹太人借钱,就拒绝跟我们这样正派的基督徒在一起吃晚饭。”
“喂,我亲爱的朋友,”贝维尔说,不自然地摇摇吊在他裤带上的一只长长的丝质钱包,“把我看作您的司库吧。两个礼拜以来,我掷骰子赢了很多钱。”
“好啰!好啰!我们别停留了,上摩尔客店去吧。”所有的青年都这样说。
营长望了望,他的兄弟还在犹豫不决。
“呃!你有很充分的时间去投交你的信。至于钱,我有;那么跟我们来吧。你也可以认识认识巴黎的生活。”
麦尔基被人家拖了去。他的哥哥替他一个个地介绍和所有的朋友见面:德·霍特罗伊男爵啦,兰西骑士啦,贝维尔子爵啦,等等。他们个个都向新来者表示亲热,迫得他要跟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拥抱起来。最后和他拥抱的是贝维尔。
“哦!哦!”他嚷道,“真见鬼!朋友,我嗅到异教徒的气味。我用我的金链打赌,赌你一个比斯托尔,你是新教派的人。”
“真的,先生,可是我还不够我理想的那么虔诚。”
“瞧瞧我能不能从一千人当中辨认出一个胡格诺来!他妈的,这些巴尔巴伊奥先生们谈起他们的宗教来,总是那么一本正经。”
“我觉得决不应该用开玩笑的口吻来谈这样的一个题材。”
“麦尔基先生说得对,”德·霍特罗伊说,“您,贝维尔,您刻薄地嘲弄神圣的事物,恐怕您要遭到不幸的。”
“瞧一瞧这个圣者的面孔吧,”贝维尔对麦尔基说,“他是我们中间放荡透顶的人,可是他还要不时地对我们传道哩。”
“让我这样子好啰,贝维尔,”霍特罗伊说,“假如说我是放荡的人,那是因为我不能够控制我的肉体;不过我至少还尊敬值得尊敬的东西。”
“我呢,我很尊敬……我的母亲,那是我认识的唯一正派的女人。此外的,我的朋友,那些天主教徒、胡格诺、巴比斯特、犹太人或者土耳其人,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我担心他们的吵嘴就像担心一个破碎的马刺一样。”
“你这是不信奉神明!”霍特罗伊嘟哝说。他在自己嘴上画十字,可是还用他的手帕尽可能地遮掩着。
“你要知道,柏尔那尔,”乔治营长说,“你在我们中间难得遇到像我们那位博学大师特奥巴尔·乌尔弗斯德尼虞那样的辩论家;我们很少进行神学的谈话,我们要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时间,谢谢上帝。”
“或许,”麦尔基面带不快地回答,“或许在你看来,你宁愿去专心倾听你刚才所提的那个可敬的牧师那渊博的议论吧。”
“别谈这些事了,小兄弟;日后我或者会再来跟你谈它;我知道你对我存了一种意见……没有关系……我们在这儿不是为的谈这类的东西……我相信我是一个正派人,毫无疑义,你总有一天会看得出来的……停止争论吧,现在该想想怎样来消遣一下。”
他把一只手掠过自己的额头上,好像要赶走一种苦恼的念头似的。
“亲爱的兄弟!”麦尔基握了他的手很小声地说。乔治紧跟着也用握手来回答他,接着他们两个赶上去同那些走在他们前面几步的伴侣重新会齐。
经过罗浮宫前面时,看见有许多打扮华贵的人从宫里出来。营长和他的朋友们差不多对他们所碰到的大人们都致礼或者拥抱。他们同时也把年轻的麦尔基介绍给那些大人,因此麦尔基在顷刻之间便认识了这个时代里无数知名的人物。同时,他也听到了他们的绰号(因为那时每一个出色的男人都有他的绰号),以及那些关于他们的不名誉的故事。
“您看见,”他们告诉他说,“这个脸色如此苍白而又如此萎黄的顾问没有?那是‘目标迷’贝特鲁斯大人;用法国话说就是皮埃尔·塞居伊埃,他无论做什么事,都非常卖力气,所以总会达到他的目标。瞧,那个小个子上尉,绰号叫作‘烧凳子’的多勒·德·蒙摩林西吧;瞧,这个叫作‘瓶子’大主教,纵使他还没有吃过饭,他依然很平直地坐在他的骡子背上。瞧,你们的教派里一个英雄,好心肠的德·拉·罗舍弗戈尔伯爵,外号叫作‘白菜的敌人’,因为在上一次战争中,由于他的眼力不好,他竟然误把一片倒霉的白菜畦当作德籍雇佣步兵,用抬枪打得它遍体鳞伤。”
还不到一刻钟光景,麦尔基知道了差不多宫廷里所有的夫人的情人和由她们的美色所惹起的决斗的次数。他了解了一位夫人名声的大小是和因为她而送死的人数的多少成比例的;因此,德·古尔达维尔夫人,由于她的情夫杀死了他的两个情敌,比起那个只引起一场小决斗和一道轻伤的德·波姆兰特男爵夫人来,声誉大得多。
一位身材很美的女人,骑着一匹骡子,有一位骑师领着它,后面还跟着两个仆人,引起了麦尔基的注意;她的衣服顶时髦,而且因为满身绣花,所以十分挺直。从这点上,人们尽可能推断,她大概是很漂亮的。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夫人们脸上都用一个假面具罩起来,她的假面具是黑色天鹅绒的。依据假面具上眼睛部位的开口处显露出来的,可以看得见,或者不如说猜得出,她大概有白得耀眼的肌肤和一对深蓝色的眼睛。
经过年轻人们面前时,她放慢了她的骡子的脚步;她甚至似乎相当注意地望望她不认识的麦尔基。在她经过的地方,看得见所有帽子上的羽毛都往地下一扫,对于成排赞赏她的人向她的致敬,她都低一低头和善地一一答礼。当她离开时,一阵轻风吹起了她那条长缎裙子的下摆,像闪电一样,露出一只白天鹅绒的小鞋子和一段几寸长的玫瑰色长筒丝袜。
“大家都向这位夫人行礼,她到底是谁?”麦尔基带着好奇心问。
“您已经爱上她了!”贝维尔嚷道,“除了谈情说爱,她从来就不做别的事;胡格诺和巴比斯特全都爱上了蒂娅娜·德·土尔芝伯爵夫人。”
“她是宫廷中美人之一,”乔治又说,“对于我们的年轻风流人们来说,是一个最危险的西尔赛。可是,不行!她并不是一座容易取得的城砦。”
“她已惹过多少场的决斗?”麦尔基笑着问。
“唔!她不过招致了二十场吧,”德·霍特罗伊男爵回答,“但是,妙处是她愿意自己亲自跟人打架:她送过一封完全合乎惯例的挑战书给宫廷里一个侵犯了她的权利的夫人。”
“怪事!”麦尔基叫喊。
“在我们这时代里,她恐怕还不是亲自打人的第一个女人吧:她送了一封写得很合适和很文气的挑战书给圣·弗娅,提议用长剑和腰刀并且只穿衬衫来跟她决一死斗,就像一个决斗专家做的一样。”
“我倒很愿意替这些夫人中的一个充当助手,为了要看看她们两个只穿衬衫的情形。”兰西骑士说。
“那场决斗有没有举行?”麦尔基问。
“没有,”乔治回答,“有人替她们做了和事佬。”
“就是他替她们做了和事佬呀,”霍特罗伊说,“他那时就是圣·弗娅的情人。”
“呸!哪儿比得上你呢!”乔治用一种很谨慎的声调说。
“土尔芝这个女人就像霍特罗伊一样,”贝维尔说,“她把宗教和社会风气搞得一团糟:她要亲自决斗,我认为这就是犯了一种死罪,而且她每天还要望两次弥撒。”
“那么,就让我安安静静地望弥撒吧!”霍特罗伊嚷叫。
“对呀,她去望弥撒,”兰西接着说,“那不过为了要在那儿不带假面具露出真面目罢了。”
“我相信就是为了这个,那许多夫人才去望弥撒吧。”麦尔基用批评口气说,他很开心找到了机会取笑一下他不信奉的宗教。
“而在新教布道场中呢,”贝维尔说,“当布道终了的时候,就熄灭了灯光,跟着就有许多美妙的事情接连发生了。该死!那真要叫我发狂地想做个路德[36]教徒哩。”
“您居然相信这些荒谬无稽的传说吗?”麦尔基用一种轻蔑的声调再说。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小个子飞兰去奥尔良听过新教布道,为的是要看看一个公证人的女人,真的,一个怪标致的女人!只要他谈起她,我的口水就涌上来了。他只有在那儿才瞧得见她;幸运得很,他的朋友中有一个胡格诺,预先把入场暗语告诉了他!他走进布道场里,请您想想看,在一片黑暗中,这个朋友做些什么。”
“那是不可能的吧。”麦尔基冷冰冰地说。
“不可能!为什么?”
“因为一个新教徒从来不会那样卑鄙去引进一个巴比斯特到布道场里。”
这句回答引起了哄堂大笑。
“呀!呀!”霍特罗伊说,“难道您相信,一个人做了胡格诺,他就不会是盗窃、叛徒、拉皮条的人吗?”
“他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兰西嚷叫。
“我,”贝维尔说,“假如我有一封情书要叫人交给一个女胡格诺,那我只好麻烦她的祭司。”
“那是因为,毫无疑义,”麦尔基回答,“你们已经习惯于委托你们的祭司干这类的事情吧?”
“我们的祭司……”霍特罗伊气得满脸通红。
“结束这些讨厌的争论吧,”乔治注意到每一句迅速的回答都带着攻势的恶毒性,便插嘴说,“我们放下一切宗派的伪善不谈了吧。我建议,此后,谁头一个再说出胡格诺、巴比斯特、新教徒、天主教徒这种字,谁就得罚钱。”
“同意!”贝维尔嚷道,“我们一会儿要上那家小旅馆吃晚饭,这人得请我们在那儿畅饮加和尔的美酒。”
出现了一阵静默。
“自从那可怜的拉诺亚在奥尔良前面被杀之后,谁也不知道土尔芝还有什么情夫了。”乔治说,他是不愿意让他的朋友们再谈神道学的问题的。
“谁敢肯定说一个巴黎的女人没有情夫?”贝维尔嚷道,“不过,柯曼治倒确实是一点不放松她。”
“就是因为那样,小个子拿哇列特才停止追求她。”霍特罗伊说,“他害怕一个这么可怕的情敌。”
“难道柯曼治也妒忌吗?”营长问。
“他妒忌得像一头老虎,”贝维尔回答,“他非要杀死一切胆敢爱上美丽的伯爵夫人的人不可;因此,为了不至于居处无郎,她不得不接受柯曼治。”
“这可怕的男人到底是谁?”麦尔基问,他对于一切多多少少有关于土尔芝伯爵夫人的事,都起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那是,”兰西回答,“我们的一个最著名的‘雅士’;因为您是从外省来的,我很愿意替您解释这个好听的名称。一个雅士是一个至善至美的风流男子,当别人的大衣触碰了他的大衣一下,当人家在离他四尺远吐了一口痰,或者为了其他一些同样合法的原因,他都会跟人打架的一种人。”
“柯曼治,”霍特罗伊说,“一天带了一个人到克列尔克草坪;他们脱下他们的短袄,拔出长剑。——‘你不是贝纳·多威臬吗?’柯曼治问。——‘一点也不是,’另一个回答,‘我名叫维尔基埃,而且是诺曼底的人。’——‘糟糕,’柯曼治再说,‘我误把你当作另一个人;但是,既然我叫了你来,我们就应该交一交手。’而他就勇敢地杀了他。”
每个人都说了一些关于柯曼治的狡猾或者好争吵的脾气。材料是很丰富的,这种谈话把他们一直引出了城外,到了摩尔客店里,这家客店是坐落在1564年开始建筑的都伊列里宫的所在地的附近一座花园中间。乔治和他的朋友们认识的许多绅士都在那儿碰头,大家就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了。
麦尔基坐在霍特罗伊男爵旁边,观察到,他一坐下来就画十字,而且眯合两眼低声地用拉丁文背诵这种奇特的祷告:
赞美归上帝,平安归生者,安息归死者,
上帝,请你可怜我们,还有
曾经孕育过上帝儿子的有福之腹。
“您懂拉丁文吗,男爵先生?”麦尔基问。
“您听见了我的祷告?”
“听见了呀,但是我坦白告诉您,我听不懂它。”
“对您说真话吧,我也不懂拉丁文,甚至这祷告是什么意思我都不大知道;不过这是从我的一位姑母那儿学来的,她经常得到它的好处,而且自从我背诵了它以来,我看到的只是功效。”
“我猜想那是天主教的拉丁文,所以我们胡格诺们,我们都听不懂它!”
“罚钱!罚钱!”贝维尔和乔治营长同时嚷了起来。麦尔基毫无难色地照罚,于是一桌上就摆满了新酒瓶,一转眼间这一群人个个都兴高采烈起来。
谈话的声音越来越大,麦尔基便趁这嘈杂的机会去和他的哥哥谈话,不再注意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了。
吃完第二道菜的时候,他们再也不能够置身事外了,因为席上有两个人开始激烈地争执,这种声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那是假的!”骑士兰西嚷道。
“假的!”霍特罗伊说。他的脸色天生是苍白的,这时简直难看得像一具死尸的脸色。
“那是女人中间最有德行、最贞洁的一个。”骑士继续说。
霍特罗伊苦楚地微笑,耸耸肩膀。所有的眼睛都瞪住这场戏的演员身上,而且似乎每个人都想静悄悄地站在中立的立场,等待着吵嘴收场。
“关于什么事呀,诸位先生,为什么这样吵闹呀?”营长问,他准备好,依他往常的习惯来反对一切影响安宁的行动。
“是因为我们友好的骑士说,”贝维尔安静地回答,“他的情妇拉西列很贞洁,而我们的朋友霍特罗伊硬说她并不贞洁,并且他很知道一些个中底细。”
立刻响起了哄堂大笑,这可增加了兰西的怒火,他那一对狂得发烧的眼睛望着霍特罗伊和贝维尔。
“我可以把她的一些信拿出来看看。”霍特罗伊说。
“我不相信你这件事!”骑士嚷叫。
“喂!”霍特罗伊带着十分恶意的冷笑说,“我马上把她的一封信念给这些先生听。他们或许都跟我一样,认得出她的字迹,因为我不认为我是唯一的该领受她的那些短信和盛情的厚赐的人。”他伸手到他的口袋里搜索,似乎要从中抽出一封信来。
“你满嘴胡说八道!”
桌子太宽大了,男爵的手够不到坐在他对面的敌人。
“我要拆穿你的假话,让你把话吞回去,一直使你透不出气来才罢。”他嚷道。说这句话时,他把一个酒瓶向他头上扔去。兰西躲过了酒瓶,但在他手忙脚乱中翻倒了他的椅子,他便奔向墙边,取下他先前吊在那儿的长剑。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有几个要加入争吵,大多数都想躲开他们。
“停止吧,你们疯啦!”乔治站到离他最近的男爵面前,嚷起来,“难道两个朋友必须为了一个不正当的女人而对打起来吗?”
“一个酒瓶扔到头上,该等于是掴了一巴掌,”贝维尔冷冷地说,“来吧,骑士,我的朋友,把长剑拔出来!”
“让开!让开!空出一些地方!”差不多所有同席的人都嚷了起来。
“喂喂!约翰诺,把门关上吧,”摩尔的店主看惯了类似的场面,无精打采地说,“要是弓手们打这儿经过的话,恐怕就要阻拦这些绅士,并且加害于这所客店。”
“难道你们要像喝醉了酒的德籍雇佣步兵们一样,居然在一个饭厅里打起架来吗?”乔治想拖延一下时间,接着说,“至少等到明天再说吧。”
“等到明天,好吧。”兰西说。他动了一动,把他的长剑插回鞘里去。
“我们这小骑士,他害怕了。”霍特罗伊说。
兰西马上推开所有站在他身边的人,直向他的敌人身上冲去。他们两个就带着盛怒相打起来;但是霍特罗伊能够及时把一条餐巾小心地围住他的左臂,巧妙地利用它来躲避对方身体的袭击;至于兰西呢,他忽略了这种防备方法,在开头几次的进攻中左手上就受了伤。不过他仍然勇敢地战斗,一面叫喊他的仆人,向他要他那把腰刀。贝维尔拦阻着仆人,说:“霍特罗伊手上并没有腰刀,他的敌人当然也不应该有。”可是骑士的几个朋友都不同意;双方交换了几句很尖刻的话,而且毫无疑义,一场决斗会转变成一场小战争,假如不是霍特罗伊对着他的敌人胸口来了一下痛击之后,又把他打翻在地上,结束这场战斗的话。他连忙一脚跺在兰西的长剑上,不让他拾起它,一面拔起自己那把长剑,想一下刺死他。决斗的法则容许这种残酷的行动。
“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敌人啊!”乔治叫喊。他从霍特罗伊手里夺走了那把长剑。
骑士的伤势并不是致命的,不过他失了很多血。人们尽可能利用餐巾来包扎了他的伤口,这时候,他带着一种勉强的笑声,从齿缝间说,事情还没有完哩。
很快地就出现了一个修道士和一个外科医师,他们为了这个受伤者互相争执了一会儿。不过外科医师有他的偏见,而且吩咐把伤者搬到塞纳河边,他就在一艘船上把伤者带走,一直到他自己的寓所去了。
仆人们有的动手拿走那些血腥的餐巾,而且洗干净被血染红的地板,另外几个在桌子上摆了几瓶新酒。
至于霍特罗伊呢,他细心地拭抹了他的长剑之后,把它插回剑鞘里,画了十字,随后,非常镇静地由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叫大家肃静,然后念出第一行,引起了哄堂大笑:
“我亲爱的,这个讨厌的骑士,他缠着我不放……”
“我们走吧。”麦尔基露出一种厌恶的表情对他哥哥说。
营长跟着他走了。那封信正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他们两兄弟虽然离席,并没有被人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