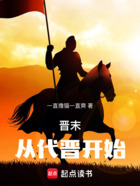
第16章 悲情英雄,京口城破
谯王司马尚之接替开口:“不若先内外戒严,防止奸细乱党。再将百官聚集一处,随时处置军情。”
他作为皇室一员,自然也是心急如焚。
以孙恩过往屠杀三吴士族的恶劣行径,一旦攻破建康,司马氏一族危矣。
“臣附议!”
司马休之是司马尚之亲弟,立即支持。
司马元显点头,这个建议还算中肯。
因南北分列及南渡问题,建康人员非常复杂,有北方各族、有亡国降将、有西域僧佛,这些都是重大隐患。
当然,历来最大的奸细,往往出自同族。
王愉紧随其后,主动提议:“应加强石头城戍防,我愿领兵前往!”
哪知司马元显摇头:“王将军坐镇京师即可,石头城由辅国将军高素去驻防。”
王愉黯然,他知道自己因之前败绩,被嫌隙了。
在王恭第二次叛乱时,他受重托,出任江州刺史,镇守寻阳,然而却疏忽大意兵败,被桓玄、杨佺期生擒。
再加上他的妻子出自桓氏,乃桓氏女婿,天然具备勾连桓氏的条件。
在这危急时刻,疑心甚重的司马元显戒备他,也实属正常。
可他不心甘啊!
一失足成千古恨。
王恺默然,他明白家弟王愉的酸楚。
自王国宝、王绪被诛杀后,如今太原王氏就他两兄弟在苦苦支撑,两人都想重振门楣。
可惜并不顺利。
此前王愉曾任三品辅国将军,他也是三品侍中,两人再进一步便是二品大员,妥妥的肱骨重臣。
但因王恭第一次清君侧时,威势太盛,骇得当时掌权的相国司马道子,只能将宠信的奸臣王国宝扔出来,安抚王恭。
二人为避嫌同父异母的兄弟王国宝,只能双双自请解职,以防遭受牵连。
后来王恭之乱平息,可他们又阴差阳错,错失机遇,如今王愉仅为四品左卫将军,他也只是五品丹阳尹。
朝中地位可谓一落千丈。
“遵令!”
高素领命,立刻前往石头城戍守。
对高素的执行力,司马元显很满意,也不枉他将其由区区庐江太守,一举拔升为三品辅国将军。
高素之所以如此受重用,是因其子高雅之乃刘牢之女婿。当初司马元显便是派他去京口,策反亲家刘牢之,致使王恭兵败。
随后,殿内像打开了阀门一般,各位朝中大臣纷纷谏言献策。
王谧、王诞一致认为应派人前往淮口,以栅栏拦截江面。
司马元显认同,随即派王诞和徐广,共同完成此项防事。
谢重也提议在长江南岸派兵驻防,司马元显命孔安国、孔靖一同前往。
两人皆出自会稽孔氏,先祖孔子,乃经久不衰的千年世家。
及至最后,司马元显将复杂的目光,投向了中护军桓脩、司徒左长史桓石生、冠军将军桓谦。
如何安排这几个桓氏的人,他没想好。
此时太过敏感,桓玄又一直在长江上游虎视眈眈,他怕腹背受敌。
三人中,桓谦好点,其父桓冲接替桓温掌舵桓氏后,一直对皇室还算忠诚,未有逾越之举。
当然,桓氏当时也不得不蛰伏起来,这点他看得很明白。
桓脩、桓石生就不好评判了。
见司马元显注意力放在桓氏身上,司马遵当即嘲讽:“你们几个桓氏子弟为何一言不发,莫非没有尽忠报国之心?”
桓脩三人脸色一变。
这司马遵当真跟狗一样,追着他们咬。
但现在当着众臣的面,还有司马元显在一旁,他们不得不表态:“我等愿意前往白石驻守。”
司马元显手指敲击着扶手,思索几人为何主动请缨去那里。殿内也随之悄然,只剩司马道子的鼾声。
良久后,司马元显没想出个所以然,只能作罢。
“那就由你们三人去白石驻防,不得有误!”
“尊令!”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姑且暂时让他们去,派几名亲信副将去监视着即可。
随着司马元显声声令下,朝中武将大臣走了一部分,剩下的人也沉默不语。
王谧看了一眼稳稳站立的谢重,有心想借机参谢琰父子一本,但何澄的前车之鉴,让他很犹豫。
谢重见王谧目光瞄向过自己,心中警铃大作,思前想后,认为他唯一能攻击的,就是谢琰父子的问题。
于是决定先发制人,堵住这鸟人的嘴。
“臣以为,在京师内,还应命中军屯兵中堂,以防不测。京师外,诏令豫州兵众前来支援,京口由刘牢之阻截,谢琰直接带兵来京师,此为最佳。”
他是想让谢琰、谢混有所作为。
此次孙恩来犯,刘牢之负主责,谢琰父子也有剿贼不力的附带责任。
只要他们领兵前来建康走一遭,介时就算护驾有功,便能功过相抵。
而且危机中潜藏机遇。
若是堂叔、堂弟拔得头筹,将那孙恩拿下,彻底平寇,立即就能受到司马元显重用,谢氏也能再列中枢!
闻言,原本藏着龌龊心思的王谧,只觉胸口发闷,接着狠狠瞪了谢重一眼。
这老狐狸,当真是一点破绽都不给他留。
司马元显目光微动,谢重的话,与王谧的神情,他都看在眼里,明白这两人在暗中较劲。
“准了,立刻传令谢琰,带兵来建康戍卫。再急讯镇北将军刘牢之,全力赶往京口,阻截孙恩!”司马元显又下一令。
对谢琰父子,他没多大敌意,毕竟并无直接利益冲突。
况且两父子此前数次大破贼寇,三吴士族眼线也汇报说谢琰主政有方,深得民心。
如此,倒不失为番镇良吏。
只是有一个消息,让他不解。
谢琰在当地广招流民,宣称是抗击孙恩,可世家大族的人又不收,这难免不让人多想。
正好,这次就借机试探下谢琰,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司马元显倒也不是觉得谢琰有异心,毕竟自谢安起,谢氏在司马皇室的口碑,很不错。
不然,也不敢让他来京师“救驾”。
而后司马元显又做了其他布置,但直到朝会结束,司马道子都未发一言,依旧鼾声连天。
司马元显有些不明所以,对先前的猜测又怀疑起来。
莫非,父王今日只是酒醉胡乱走走?
两人对面,司马德文眼中一丝愠怒一闪而逝,随即恢复平静。
…
前往白石山的路上,桓氏三人领兵疾驰。
一侧的桓石生,一边扬鞭,一边愤愤不平狂吼:“司马遵这狗东西,每次碰到我等,都要出言相讥。”
桓谦也沉着脸,不太高兴。
他父亲桓冲官至太傅,对司马皇室一直恭敬有加。
那武陵王司马遵的老爹,是大伯桓温废黜的,又不关他这一脉的事,居然也将他和弟弟桓脩一并羞辱。
而桓脩抓着缰绳,控制马匹方向,心中却在想着舅舅王诞曾透露的消息。
几月前在司马元显府上,这司马遵便向司马元显提过“革职并驱逐朝中桓氏子弟”,当时堂舅王谧就在场,听得清清楚楚。
可见司马遵不只是言语讥讽,已经开始针对他们了。
这事他暂时都没敢告诉堂弟桓石生,不然以他的脾性,指不定闹出什么幺蛾子。
桓石生见两个堂兄并未搭话,眼睛转了转,故作随意地说道:“这大晋如此风雨飘摇,国祚不知尚有几何?”
桓谦轻声呵斥:“堂弟慎言!隔墙有耳!”
桓脩亦是小心张望,左右看了看,见护卫兵离得较远,暗自松了口气。
司马皇室这般防备桓氏,堂弟桓玄似有不臣之意,若是桓石生的言论再被传出去,那他们这群在京师的桓氏子弟的处境,已经可以想象的到。
司马元显必定严加防备,甚至暗中命人监视他们。
并且,他与桓谦乃亲兄弟,家眷皆在京师,一旦发生什么,全家逃都逃不掉。
哪知桓石生闻言后,却丝毫不在意:“愚弟说的本就是事实,两位兄长何必这般惊慌。”
桓谦与桓脩互相交换了下眼神,并未再说什么。
但两人心中已决定,得与桓石生保持距离,以免发生不可控的意外,被其牵连。
桓石生看二人反应,暗自冷笑。
身为桓氏子弟,岂是你们想置身事外,就能遂意的?
自己已将孙恩来犯的消息,传递给桓玄。
想来这位好堂弟,收到消息后,会有所动作吧?
到时场面一定很精彩,哈哈哈。
...
就在孙恩剑指溯江而上的当日,京口就在紧张戒备。
此时留守的是孙无终、毛德祖等人。
刘牢之是去吴郡抢军功,自然要带亲信人员,至于孙无终,当然被排除在外。
“孙将军,贼寇有近十万之众,离京口已不足五里!”
参军毛德祖急忙向孙无终报告军情。
身材魁梧的他,将近八尺的身高,加上一张国字脸,看起来很有忠义的气质。
毛德祖也确实忠义。
后面随刘裕南征北战,参与平定卢循、征讨荆州、攻灭后秦,为刘宋开国功臣,刘裕称帝后,毛德祖长期镇守虎牢关。
在北魏趁刘裕身死,兵发刘宋时,毛德祖据守虎牢关,数次打退敌军。
最后迫使魏主拓跋嗣御驾亲征,领着整整半个北魏的兵力,围攻虎牢关。
而刘宋当时的皇帝刘义符,沉迷于男色不可自拔,荒于政事,朝廷未能及时支援毛德祖。
拓跋嗣见久攻不下,命人断绝水源。
好在虎牢关山上有一口深达四十丈的水井,能继续支撑。
然而拓跋嗣非常狠,得知山中水井位置后,命人直接拦腰凿开虎牢山,掘地道直通井体,将水井封堵。
最终山上军队因缺水,关隘被破,毛德祖被俘,客死北魏。
当时缺水到什么程度,毛德祖的士卒受伤后,血都流不出来!
但他们依然为身后的刘宋,抗争到最后一刻。
可惜,毛德祖孤军奋战时,檀道济、沈叔狸、王仲德所率领的足足三路大军,都不敢去救援。
可悲,可叹!
“命楼船出击,给我狠狠撞碎这些杂碎!”
孙无终是经历过铁血场面的,当即毫不犹豫下令。
随即,横于江面的几艘高大如城堡的楼船,在木板船的牵引下,开始顺江而下,直冲孙恩船队。
一刻钟后,两军相遇。
二十余丈长,高出水面两三丈的楼船,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将渔船、艨艟瞬间荡平几十艘。
上千贼寇落入江水中,随波涛翻涌。
楼船上的士卒也趁机用箭矢、长矛,收割一个个贼众,江面泛起片片血花。
“灵秀,官军水师太过强悍,我们这样必败。赶紧命部众弃船上岸,直取京口军府。”徐道覆见己方在水战上,不是一合之敌,立刻献策。
孙恩也明白陆战才有优势,当即喝令信众们划船登陆。
几千艘船慌乱转向,靠向岸边。
好在这些部众、信徒都是三吴之地的人,水性、船只掌控都还可以,虽然混乱,倒也并无多大伤亡。
待到岸上,依旧还有七八万人之多。
而京口驻防士卒,仅万人,悬殊有点大。
两军于陆地上刚一接触,双方便死伤无数。
北府军辅以床弩、强弩,射杀不少前排贼寇。
但贼寇也不是吃素的。
有悍不畏死之人,趁着弩箭填装间隙,冲进北府军中。
也有人驱赶普通百姓做掩护,攻入官军队列。
并且,往往四五个人围攻一名北府兵,死了一批,另一批又补上。
任凭北府士卒再凶悍,总会被车轮战耗死。
好在京口重镇有不少陷阱、堡垒,此外还有一座位于北固山的铁瓮城。
孙无终见势不利,在牺牲两三千人后,率余众避于城中。
此城规模不大,南北长约五百米、东西最宽处约三百米,但胜在乃是包砖城墙,内外皆固以砖壁。
孙恩想攻破此城极为困难。
可贼寇的目的并非是破城,而是肆虐京口,抢夺钱粮、武器、裹挟更多部众。
因此,京口军固守铁瓮城,对孙恩影响不大。
他命三万人围而不攻,又让其余人全速前进,沿京口一路烧杀抢掠。
龟缩于城中的众将士,目眦欲裂。
他们的家眷皆居于京口,已在当地落地生根多年。
此时被贼寇无情屠杀,顿时纷纷请命出战。
“将军,就让我等出城与贼人决一死战!”
“对!脑袋掉了碗口大个疤。”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大不了人死鸟朝天!”
孙无终怕军队哗变,不敢继续压制士卒,无奈只能下令出城迎击。
此举正中孙恩下怀。
最终,大量北府军阵亡,孙无终、毛德祖仅带一千余众,突出重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