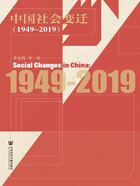
一 社会变迁的中国路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践路径,在相当程度上与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实施的社会建设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并由此塑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关系格局。这些不同阶段分别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这三个历史阶段,党和国家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势与趋势,在社会建设中适时调整和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从而影响了我国社会变迁的走向。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中国实现了主权独立并从此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新中国在社会建设上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团结稳定的社会秩序。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种种困难(如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建构了包括单位制、人民公社制以及街居制、户籍制等一系列制度在内的制度架构,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体主义至上的意识形态和延续30年的总体性社会体制。在当时短缺经济的背景下,国家基于这一体制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以保障民生,对社会生活进行规训并对社会保障运营进行管制。随之,人们的社会心态从革命战争时期的震荡逐渐转变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忱。在此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浮躁问题,对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总体而言,这一社会体制与当时社会生活的组织状况是相适应的。
总体性社会体制虽然有助于解决1949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由此而生。改革开放前,持续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管制难以为继,改革社会体制模式成为必然选择。党和国家审时度势,直面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的状态,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再到90年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赢得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05年以来,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增量改革的同时,党进一步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建设计划,通过取消农业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使得社会民生在整体上持续改善。在全民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大环境下,从市场中释放的活力溢出至社会领域,社会主体开始觉醒,在表达社会诉求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社会力量得以发育,社会自主性明显增强。与此同时,社会关系结构、社会心态与社会预期,以及社会认同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进而推动社会转型进一步加速,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被提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科学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主要特征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新内涵和新要求。与此同时,快速转型中的社会变迁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仍在持续,而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双重分化,人们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社会的去组织化持续发展;原先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累积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我国社会变迁的现实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和国家在战略层面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四个全面”的贯彻落实,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及其新格局的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重构,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问题来重塑社会认同。
近些年来,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而复杂的分化,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团结纽带再次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正在发生的产业关系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特别是劳动关系的变化,新业态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职业群体的身份和社会关系逐渐模糊,用传统的劳动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难以理解和回应这些重要的变化。中国网民由1997年的62万人激增至2018年的8.3亿人,年均增长40.9%。其中,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4G网络覆盖率的提高,各类出行、餐饮外卖等移动应用加快普及,带动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高速增长。2018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711亿GB,是2013年的56.1倍,5年来年均增速高达123.8%。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快递业在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异军突起。我国快递业务量在2014年首度超过美国后,持续保持世界第一。[4]
大数据、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成员的联结方式,进而有可能推动形成新的社会结构。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各领域跨界融合,催生一系列“互联网+”经济新业态。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成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持续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形成一批行业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消费持续释放居民需求潜力。截至2018年末,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达6.1亿人,占网民总体的73.6%。[5]信息技术的高度渗透,一方面使得实体社会与网络虚拟社会的边界难以界定,更加模糊;另一方面又让网络虚拟社会的实体化趋势更加明显。这种实体化在对社会态度、社会预期的影响上明显具有许多新的特征,比如,有时表现为对阶层界限的消解,有时又明显地具有强化阶层内聚力的特征。典型的现象如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上舆情态度的分化。另外,由于信息技术等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的变革,更多的平台化的生产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所看到的生产关系,即传统工业流水线上基于契约的生产关系等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核心特征表现为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去结构化、去组织化,更加凸显个体化的特点。典型的现象如卡车司机群体难以形成工会。[6]与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变迁等因素相联系,中国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职业不能简单地以收入水平、教育与人力资源水平、稳定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等为测量指标。职业结构的灵活性、弹性、可变性等也会影响人们的就业选择和就业预期:一是就业渠道多元化。通过进入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及自主创业和各类新就业形态实现就业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就业。二是就业形式多样化。许多新就业形态不再有硬性的时间、地点限制,如兼职就业、网络平台就业等就业形态不断出现。三是就业观念市场化,劳动者愿意为获得就业岗位或更高的收入而进行流动,打破了城乡、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的界限,自主择业、自主创业、终身学习等新就业观念也越来越流行。[7]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70年来,党和国家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路径。改革开放以后,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信息化等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不断加速,并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就中国社会变迁而言,我国社会体制从大包大揽的总体性社会体制,逐渐转变为放权让利、不断激发市场和社会发展活力的多元化社会体制,人们的生活从缺衣少食、温饱不足转变为品质提升、小康富裕;中国社会从低水平上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向高水平上不断回应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转变。上述各个维度,共同凸显了基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变迁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