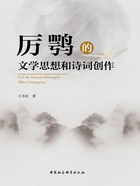
第一章 厉鹗的生平、思想与著述
第一节 厉鹗的生平
厉鹗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在野”色彩的著名学者兼文学家,观其一生,没有建立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也未亲历过惊涛骇浪般的政治事件,更没有担当天下的经世之志,对当时严酷的政治文化高压也没有作出过任何激烈甚或是明显的反抗。但是,厉鹗和他的浙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之下,属于极为特异的一个群体。这一群体隐然与王朝处于离心状态之中,尽管没有明显的反抗斗争,但这一群体的存在本身在号称“盛世”的雍、乾时代显得是那么不协调,甚至刺眼!作为以布衣为主体的清代中期浙派,其宗主厉鹗恐怕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布衣之一。关于厉鹗的生平便从这里讲起。
清朝康熙三十一年(1692)五月初二日辰时,在浙江杭州城东东园的一个农家,一个男婴出生了,这家的女主人被称作何孺人,二十三岁得一子,自然欢天喜地。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著名诗人和学者厉鹗,他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从厉鹗的名字看,无论是他的家人还是他自己,都想让他有一番作为,然而不幸的是,他不但生活在极度专制的雍、乾时代,又出身于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这两点可以说缠绕了厉鹗的一生,他不能脱离严酷的时代,更不能摆脱终身的贫穷。其实厉鹗的祖上曾居住在慈溪,后来迁到钱塘,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布衣,他在家里排行第二,兄名士泰,弟名子山。由于父亲去世早,长兄为父,士泰便担负起养活一家老小的重任,但只靠卖烟叶过活还是有困难。无奈之下,士泰便提出将厉鹗寄养到“僧寮”的动议,厉鹗“不可”,士泰只能作罢。[1]就在这样的贫困境遇之下,厉鹗一天天长大。到他十六岁时,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厉鹗迎来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这年,他结识乡里贤达杭可庵并从之游。这位可庵先生,便是后来成为大学者和大名士的杭世骏的父亲,厉鹗因此也与杭世骏成为终身不逆的挚友。在刻苦学习的同时,厉鹗还广泛出游,增长见识,在这两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之下,厉鹗在十九岁时就写出了非同凡响的《游仙百咏》,初步显示了他特殊的文学才能和高超的想象力。在诗中,厉鹗似乎对当时现实有所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能仿古人诗体,来抒发自己的感愤。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又连续写了《续游仙百咏》《再续游仙百咏》,这样,《游仙百咏》共三百首,成为他作品中的巨制。他自己对此也颇为满意:“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将以予为厉游仙乎?”[2]
康熙五十三年(1714),厉鹗二十三岁,这年,厉鹗实现了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由求学转变为坐馆先生。他教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著名学者、诗人汪沆及其兄汪浦。汪氏家筑有听雨楼,书香古朴,书声琅琅,厉鹗与汪氏兄弟亦师亦友,学习、生活十分惬意。这样的日子过了五年。在这五年内,厉鹗结交了金农、周京等诗人,并在二十五岁时结婚,娶蒋氏。需要指出的是,蒋氏一生未育,厉鹗将此事视为终身的遗憾。
康熙五十九年(1720),对二十九岁的厉鹗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他参加了乡试,以第四十九名中式。当时的主考官是江西临川人李绂。李绂见了他写的谢表,叹道:“此必诗人也。”[3]并立即录取。厉鹗于同年北上入京参加会试。因为是第一次入京,作者的心情是愉快的,一路上,他“出莺脰湖,道经姑苏新丰(即今丹阳)、广陵,到宝应,渡河上宿迁、郯城,过沂水,历半城、蒙阳、羊流店拜羊太傅祠,入泰安,道中望岳作歌,晚次齐河,除夕始抵德州”[4],这次长途旅行大大开阔了厉鹗的视野,他写了许多诗。在京城,他的诗受到吏部侍郎兼掌院学士汤右曾的赞赏。但不幸的是,这次考试失利。汤右曾想把他请到府中,但“樊榭为人孤僻,次晨遽束装不谢而归。说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贤樊榭之不因人热”[5]。回到杭州后,厉鹗诗名大振,与当地的许多志同道合者结成诗社,频繁唱和,如金志章、周京、金农等人。另外,结识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也是厉鹗在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二马”在物质上经常接济贫困的厉鹗,更重要的是马氏将自己的藏书无条件地供厉鹗阅览。“扬州二马”筑有小玲珑山馆,内有聚书楼,藏书极为丰富。正是利用马氏丰富的藏书,厉鹗写成了《宋诗纪事》等煌煌巨著。在著书之余,厉鹗与二马等人谈诗论文,考证文物,切磋学艺,结韩江诗社,“觞咏无虚日”[6],后来全祖望也加入。除此之外,雍、乾之际,厉鹗撰写了《南宋院画录》八卷,《东城杂记》二卷,《湖船录》一卷和部分词作,并与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赵信共同撰写《南宋杂事诗》七卷。
雍正九年(1731),厉鹗四十岁,时任浙江巡抚的程元章聘厉鹗、杭世骏、沈德潜、张云锦、吴焯、赵信等二十八人分修《浙江通志》。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发达”的沈德潜与厉鹗在修史之余谈文论诗,意见已见分歧。袁枚就说:“吾乡厉太鸿与沈归愚,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7]这次修志,“越二年始削稿,又一年剞劂蒇事”[8]。
乾隆元年(1736),樊榭受浙江总督程元章之荐(此次共举荐十八人,包括杭世骏、汪沆、钱载等人)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博学鸿词科自康熙十八年(1679)开科以来,对消弭汉族士人的离心力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以考试之名,行拉拢之实。如果说清初政治尚不统一,文化上难施高压,这种考试尚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而到乾隆时代,文治武功既已奏效,领土已归于统一,文字狱的打击既已使士人噤若寒蝉,博学鸿词科考试早已失去其本意而“变味”,徒然成为示恩的手段。对厉鹗来说,这次考试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入京参加科举考试。本来以厉鹗的天性,无意于此,但他的好友全祖望这时特地从京城写信劝他,要他“与堇浦诸君勉之”[9]。迫于挚友的热忱相劝,樊榭参加了这次考试。在这批征士中,樊榭的才华是出类拔萃的,杭世骏曾说:“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胡天游)之古文,绍衣(全祖望)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10]这话绝非虚语,此三人皆为浙人,稚威为胡天游,山阴人,绍衣为全祖望,鄞县人,皆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但这次考试,樊榭因误写格式而落选,实为憾事。这次落选后,厉鹗已经四十六岁,开始步入老年了,这时期的厉鹗似乎更贫困,健康状况也大不如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膝下无子的隐痛也时时折磨着他。
这时候,一位名叫朱满娘的女性进入了他的生活。她的出现,给这时期的厉鹗的生活和创作都打上了强烈的亮色,也是他一生中最富色彩和诗意的时期。两人感情非常深挚,厉鹗对朱氏极为欣赏:“姿性明秀,生十有七年矣。……姬人针管之外,喜近笔砚,影拓书格,略有楷法。从予授唐人绝句二百余首,背诵皆上口,颇识其意。每当幽尤无俚,命姬人缓声循讽,未尝不如吹竹弹丝之悦耳也。余素善病,姬人事予其谨。”然而不幸的是,在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在厉鹗五十一岁时,朱氏病逝,年仅二十四岁。这件事对厉鹗打击很大,“悲逝者之不作,伤老境之无悰,爰写长谣,以摅幽恨”[11]。翻检厉鹗后期诗词创作,有多首为伤悼朱氏而作,甚至在朱氏病逝数年之后,仍然悲伤不已,作诗纪念。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诗词,应该说是厉鹗创作中表达最见直接、感情最为剔透的作品之一,此类诗曾大受袁枚赞赏,很有价值。
晚年的厉鹗患有牙疾、足痛,甚至肺部也有隐疾,并且经常靠典当家俱、出卖书籍维持生活,可谓贫病交加。但这阶段,厉鹗的学术研究却可谓硕果累累。著名的《宋诗纪事》一百卷和《辽史拾遗》二十四卷都完成于这一阶段。两部巨著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厉鹗的晚年尚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乾隆十三年(1748),樊榭已经五十七岁了,却“忽有宦情,会选部之期近,遂赴之”。这次,他的诸多好友如全祖望等都劝他,不必以“素丝”“清才”应选一区区县令。樊榭答曰:“吾思以薄禄养母也”[12],既是为了养母,同仁不好再劝阻,厉鹗遂北行。北上入都时,谢山相送,赠诗云:“尔才岂百里,何事爱弹冠?鱼釜良非易,茧丝亦大难。瘦腰甘屈节,薄禄望承欢。倘有清吟兴,休从薄牍兰。”[13]然而当他北上到达天津时,老友查为仁留他住在水西庄探讨艺文。查为仁即著名的“南马北查”中的“北查”,亦藏书丰富,好结交文士,与“南马”(扬州二马)一样,是在当时凄凉时世中,与贫寒文人推心置腹、相濡以沫的著名人士。当时,厉鹗是临时路过住在他家里,看见查氏为南宋周密的《绝妙好词》所作的笺注,分外高兴。因为樊榭也对《绝妙好词》有极大的兴趣,并曾经收集过有关《绝妙好词》的材料,做过一些研究。这时他想的是:是和查为仁合作完成一部巨著,还是入都铨选区区一介县令?最后,他决定留下来,和查为仁同笺《绝妙好词》,数月之后,全书完成,返回杭州。谢山听到消息,戏之曰:“是不上竿之鱼也”[14],并欣然作诗一首:“慈亲年八十,捧檄已非时。大有陟陔乐,长吟投芾诗。悲秋笠泽鲙,招隐小山枝。兴尽翩然返,从今保素丝。”[15]谢山不愧为樊榭的知己和“石友”,以樊榭入仕为忧,而以樊榭全身而归为乐!
另一件事是,乾隆十六年(1751),也就是樊榭去世前一年春三月,乾隆皇帝弘历奉太后南巡江、浙,樊榭和吴城(吴焯之子)共撰《迎銮新曲》进呈乾隆,吴城曲为《群仙祝寿》,樊榭曲曰《百灵效瑞》,此事在当时很有影响。
乾隆十七年(1752)九月,樊榭病重,十日,以文稿二册授弟子汪沆,曰:“予生平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索序。诗词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册藏敝箧,子知我者也,他日曷为我序而存之。”[16]汪沆泣而受命。十一日辰时,樊榭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一岁。身后八十老母尚存,备极萧瑟。
樊榭去世后,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巨大悲痛,前后写挽词吊唁者二十九人。一方面,他们感叹从此失去了一位挚友;另一方面,叹惜诗坛失去了一位领军人物。事实上,在厉鹗死后三年,马曰琯亦去世,江浙诗社活动也逐渐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