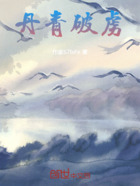
第4章 初到灵隐寺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莫欺少年穷,十年归报楚人仇。”
此后半月,按照师傅说的线路,李丹青背了包袱,杵了木棍一路向北。他白天赶路,晚上歇脚,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采野果充饥。偶尔路过集镇,他会买些馒头大饼,以备不时之需。
终于,李丹青一路问询着来到了万源县境内。离开军阀杨森实际控制的地盘,他放下戒备大摇大摆的走在官道上。然而,路上来往行人脚步匆匆,却让李丹青感到有些疑惑。于是,他寻着路边有一位歇脚的中年人闲谈起来,“大叔,我是外地来的,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中年人身形佝偻,背着一背洋芋靠在路边的青石上休息。他看李丹青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也没有什么恶意,于是略带气喘地回答道:“这里是万源县的五宝镇。”
“五宝镇,名字很特别呀。”
中年人脸上露出了一丝自豪的笑容,解释道:“我们这里虽然穷困,但是洋芋、魔芋却多得是。山里还有天麻、香菇和木耳,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贝。所以,这里就被称为五宝镇了。附近的万州和开州的商贩都会到这里来买山货。”
李丹青点了点头,继续追问道:“现在不是农忙时节,为什么这些路人都来去匆忙呢?”
中年人叹了口气,说道:“小兄弟,你还是快点赶路吧。刘存厚和杨森天天打仗,这里是他们地盘的交界处。往北是五宝镇,往南是开州的高桥镇。一旦打起仗来,边界上就会设卡,过往行人一律不准通行。搞不好还会挨枪子呢。你还是快点走吧,我也要赶紧把洋芋背到五宝镇去卖了。”说完,他弯着腰背起背篓,大步朝前走去。
李丹青刚才从高桥镇过来时,的确远远的看见官道上一些背着枪的大头兵设卡盘查。当时,他担心着惹上麻烦,还故意绕行了很远。此刻听大叔提起边界的局势,不由加快了脚步,生怕因禁止通行而耽误了行程。
两个时辰后,李丹青赶到了五宝镇。一截土围子城楼上斜斜的插着一面土黄色的龙旗,上面一个大大的“刘”字赫然在目。城门楼子下,一队官兵设了路障,正在排查过往路人。李丹青心想着进入了刘存厚的地盘,也放下了戒备,跟着人流站进了等着进城的队列中。
一个大头兵刚搜过一位长衫书生打扮的中年人,见书生身无一物,也没了兴趣,不耐烦的说道:“走吧走吧,到前面交两个铜子。”
书生不解,“进城为什么还要交钱呀?”
搜身的士兵瞪了他一眼,语气中带着几分火气:“你新来的吧,不知道规矩呀。这是路桥税。”
“这是哪门子规矩,不明抢吗?”书生眉毛一横,不服气的说道。
士兵顿时火冒三丈,冲城门处嚷道:“关排长,这里有个刺头不肯交钱!”
城门旁,一军官模样的胖头男人正仰着身子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听到士兵的呼喊,他慢慢起身,揭下帽子,踱步走了过来。紧接着,军官围着书生上下打量一番,冷冷的说道:“再给你一次机会,别说我没提醒你呀,信不信军爷我把你以通匪罪就地枪决。”说完把帽子递到书生面前。
书生此刻又气又恨,但又无可奈何。自古以来,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在军官赤裸裸的威胁下,书生最终只能不甘地往军帽里扔了两个铜子。
看着泛黄的铜子蹦跳着落入帽子,军官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道义和礼法在强权面前都是扯淡,只要手里有了枪,这个世上便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军官对这个世道简单的理解。
军官冷哼一声,摸出军帽里的两个铜子,放入兜中,随后重新戴上帽子,背着手在排队的人群中悠闲地转了一圈。他扯开粗哑的嗓子,大声宣布道:“从明天起,这里的路桥税涨到三个铜钱一次。”
话音刚落,人群立刻骚动起来。几个胆大的民众开始发声抗议,“又涨呀,这才几个月呀,怎么涨得这么快!”
“是啊,我这一捆柴才换五个铜钱,你们就要收三个,这还怎么活呀!”
“三文一次,这不是要逼死人吗!”
“太过分了,还有王法吗?”
军官冷眼扫视过人群,嘴角一撇小胡子微微抖动,不屑地说道:“在五宝镇,我就是王法!你们这一帮穷鬼,没有老子在这里守着,杨大头的部队早把你们抢得个子没有,到时死了都没人收尸。今后就这规矩,要么你就不来,来了不交税的就以通匪论处!”
虽然人群中仍有人愤愤不平,但在军官的威势之下,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他们明白,在这个乱世之中,弱肉强食是常态,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低头。
李丹青乖乖交了两个铜钱后,顺利进了城。这是个边陲商贸小镇,从街道两边招牌林立的各式店铺,依稀可见这里曾经的繁盛。然而,随着近年杨森和刘存厚交恶,镇上的情况也急转直下。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早已搬到别处躲避战祸,只留下一些迫于生计的寻常百姓还在苦苦坚守。临街的门店大多关门闭户,鲜有顾客。城门处的官兵盘剥过往商旅,更是加剧了镇上的萧条。
李丹青走在大街上,只见稀稀拉拉的几人走动。而那些吊儿郎当的游兵散勇还时不时的出现在街头巷尾,给小镇增添了一抹不安的气息。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开门营业的饭馆,李丹青买了些馒头后,便和店里的伙计问询路程。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他已经在荒郊野岭中住了几日,虽然绕了不少弯路,但也慢慢摸清了赶路的门道,长了不少经验。
长途赶路时,方向感至关重要,尤其是不能错过宿点。虽然李丹青囊中羞涩,住不起旅店,但他深知睡在村镇里远比野外要安全得多。回想起之前因错过宿点而遭遇的惊险经历,他至今仍心有余悸。
有一次,因为错过了宿点,他不得不在一个山坳里过夜。夜里,刺骨的寒风夹杂着瓢泼大雨,让他狼狈不堪。直到第二天天亮,他才发现自己竟在一处荒野坟地中过了一夜,现在想起都觉得毛骨悚然。还有一次,他睡在山梁子上的黄桷树上,半夜时分,四周响起了嗷嗷的狼叫声,叫得人瘆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握了把柴刀,紧抱着树枝,一晚上都没敢合眼。
此时已过申时,李丹青估算着到前面一个镇子还需差不多三个小时的路程。只要不走错路,天黑时便能赶到。不过,他心中清楚,灵隐寺已近在咫尺,也不急着冒了风险赶这一日两日。于是,他随意的在街上转悠着,想寻一处遮风挡雨的落脚点。
漫步在街道上,李丹青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路边一对乞讨的祖孙身上。一个瞎眼的婆子,领着一个两三岁的孩童,两人相依为命。老人头发花白,颧骨突兀,眼眶凹陷,嘴唇干涩发裂,犹如枯树根般的右手举着一只破碗悬在半空。孩子则无力地侧躺在老人身边,空洞的眼神呆望着来往的路人。
李丹青心中涌起一阵怜悯之情。他深知,但凡有条活路,谁也不愿意这样卑贱地活着,不仅受人白眼,还与狗抢食。想起自己跟随柱子流落街头的日子,他对这些乞丐的遭遇更是感同身受。虽然自己的能力有限,也不可能帮了他们一辈子,但每次遇到乞丐,他都会力所能及的给予一些帮助,哪怕只能让他们勉强吃饱一顿半餐,也会觉得心里好受些。
李丹青从包袱里取出两个馒头,轻轻放在老人的碗里。感觉到面前有人,举起的破碗里好像忽然有了重物,老婆子风干打皱的脸庞露出一丝喜色,急忙牵了孩子给他磕头,“谢谢啦!谢谢啦!菩萨会保佑你的!”
“哎……”李丹青无奈的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去。
这世道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地主吸血,仿佛到处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就连乞丐堆里,也是弱肉强食,无数人像蝼蚁一样活着,每日里食不果腹、朝不保夕。李丹青一路走来,目睹了民生的疾苦,也看到了骄横暴虐的恶人。
他是善良的,眼里充满了对穷苦百姓的同情;他也是正直的,对兵痞、土匪和那些无良的地主怀有满腔的愤怒。然而,他更明白,在这乱世里,只有拳头才是硬道理,无端出头只是不自量力。在黑洞洞的枪口下,血淋淋的刺刀前,真理、正义、勇敢、善良就留着对阎王去说吧。因此,他选择了聪明的活着,理智的善良,在他没有成为上帝之前,他拯救不了世界。
正当他低头思索间,前方路口突然传来了尖叫声。
“啊——你干什么?放开我!”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被三个身穿军装的人堵在了巷口,嘴里惊恐的喊叫着。
那姑娘身着淡粉色花布棉袄,领口和袖口都绣着精致的云纹,朴素又不失雅致。她的面容清秀,皮肤白嫩,一双杏仁眼此刻正满含惊恐与愤怒,仿佛两颗晶莹的露珠在晨曦中颤抖。一根麻花辫子垂在肩头,随着她的挣扎轻轻晃动,更显得她娇小无助。
三个兵痞此刻已将姑娘围在中间,他们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目光在她身上肆无忌惮地游走。而姑娘此刻早已是满脸通红,眼中满是惊恐与无助,芳心大乱,仿佛一只受惊的小鹿。
“你喊什么呀,你撞了人,难道不该道个歉。”一个穿着军装的高个子士兵歪着脑袋,晃着腿,一脸坏笑。
姑娘气愤的反驳道:“明明是你撞的我,怎么恶人先告状呀。”
我撞你?笑话,你哪只眼睛看到的?”高个士兵揶揄一笑,转头问向旁边的两个同伴,“你们看到没有?”
“没有啊,我看见她撞到你呀。”一旁的士兵满脸邪笑的附和道。
“你们是一伙的,当然帮着说了!”姑娘试图推开围住她的士兵,想要离去,“起开!我要回家!”
高个士兵迅速迈前一步,挡在女孩身前,后面的士兵顺势一推,小姑娘毫无防备地撞在了高个士兵身上。
高个士兵佯装疼痛,嘴角挂着一丝痞笑,说道:“你看,你又撞到我了。”
小姑娘气得原地跺脚,眼中泛起了泪花,略带哭腔地喊道:“你们无赖,无耻!快让开,我要回家!”
高个士兵假装关切地凑近,嬉皮笑脸地说道:“哎哟,小姑娘,别哭嘛。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只要你喊声相公,我就放你回家,怎么样?”
旁边的士兵也跟着起哄,哄笑声中充满了恶意:“对,喊相公,这事儿就算扯平了。”
“你们流氓!我不喊!”小姑娘又气又急,声音颤抖。
“不喊可不行哦……”高个子士兵一听,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淫邪起来,一双咸猪手伸向小姑娘,在她身上肆无忌惮地揩油,引得小姑娘连连尖叫。
李丹青只匆匆看了两眼,便明白了眼前的状况。他愤怒地举起拳头,但随即又理智地缩了回去。他清楚,以自己瘦弱的身板,贸然上前不仅无法救出小姑娘,还可能无端遭受一顿毒打。
他皱起眉头,心中焦虑不已,思考着该如何替小姑娘解围。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好似想起了什么,转头快步折返了回去。
这里较为僻静,小姑娘被三个士兵围住,你一言我一语地调戏着。偶尔有一两个路人经过,也都怕惹麻烦,远远地绕开。小姑娘满脸煞白,双手紧紧抱在胸前,无助地被三个士兵哄笑着推来推去。
这时,街边走来一个瞎眼老婆婆,一手拄着木棍哒哒哒地探路,一手牵着一个三岁的小孩。两人摸索着走到高个士兵身边。高个子士兵本已让开,但老婆子还是突然身子一歪,倒在地上。
高个士兵不明所以,看了一眼地上的老婆子,又看向同伴,犹豫间却被老婆子紧紧的抱住大腿,“撞倒人了,别跑。”
“谁撞到你啦,你不要血口喷人!”高个士兵使劲的甩着腿,想把老婆子甩开,无奈老婆子用尽了全身力气在手上,任凭高个士兵怎么折腾就是不松手。
“再不松手,老子可打人了哈。”高个士兵没想到被一个叫花子“碰瓷”,满脸厌恶的威胁道。一旁的士兵也蹲下身子,使劲的搬开老婆子紧扣的手指。
老婆子俯在地上双腿乱蹬,嘴里大叫道:“当兵的打人啦!当兵的耍流氓啦……”
而那三岁小孩早在一边张嘴大哭起来,哭喊中顺势倒在地上满地打滚,“不许打我外婆,不许打我外婆!”
高个子听见老婆子的喊声险些晕倒,你说打人倒是可以接受,可是偏偏老婆子还说他“耍流氓”,简直让他觉得威名扫地。今后在军营里传开,自己居然对一个五六十的老婆子耍流氓,还不叫人笑掉大牙?
这就叫用无奈对付无奈,用卑鄙对付卑鄙。李丹青躲在街角看着这滑稽的一幕,捂着嘴咯咯直笑。眼看几人在原地纠缠不清,再不出场,老婆婆可真要挨打了。他清了清嗓子,从街角跑出,扬声大喊:“当兵的打人了!外婆你别怕,我已经喊人来了,二叔、三婶马上就过来!”
几个当兵的看对方还有人来,害怕事情搞大了脱不了身,说不定还要挨打赔钱。人家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看来这当兵的遇到老婆子也是有理说不清。几个士兵现在已无心寻花问柳,只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老婆子听见李丹青的声音,也松开了手。三个士兵如获大赦,抽身拔腿就跑。
李丹青先是上前扶起地上的老婆婆,“没伤到吧?”
老婆婆揉了揉胸口,笑道:“不打紧,就是被踹了几下,能救下这闺女也值。”
小姑娘此时也明白了眼前几人演了这出大戏都是为了救下自己,连忙上前握着老婆婆的手,感激涕零地说道:“真是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帮忙,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完,她又小声抽泣起来。
老婆婆握住姑娘的手,怜爱地说道:“没事就好,这兵荒马乱的,今后姑娘家出门可得小心点,老婆子救得一次,可救不了第二次哦。”
李丹青也在一旁安慰道:“姐姐,真要道谢的话,今后在街边遇见她们时,多给几个馒头就行。时候也不早了,你就赶紧回家吧。”小姑娘轻咬着嘴唇,连连点头。
送走了小姑娘,李丹青扶着老婆婆来到一所破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两人道了别,李丹青重新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又行两日,李丹青沿路打听,终于来到了烟霞山山脚。他抬头仰望着眼前的高山,只见山体挺拔俊秀,山势延绵起伏不见尽头。李丹青寻了根木棍做拐,沿着崎岖山路一路攀爬。山间树木青翠,古树参天,烟雾弥漫,宛若人间仙境。偶有山涧溪流潺潺流过,虫鸣鸟叫,让人顿觉神清气爽。
途中偶遇林间打草砍柴的山民,李丹青攀谈得知,烟霞山位于大巴山和秦岭交汇之处,群山叠嶂,莽莽数十里。高大的秦岭阻绝了北方寒气,冷暖空气在此汇聚,才生成了早间起雾,晚间生霞的奇异景象。而灵隐寺便位于烟霞山山顶,只有少数本地人才知道此处寺庙,因此那里人迹罕至,少有香火。
约摸小半天,李丹青依着山民所指方向,终于到达灵隐寺门前。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有些失望。他原本想象中的灵隐寺应该是高大巍峨的山门,红墙碧瓦的围墙,庄严肃穆的佛像,然而眼前的寺庙却与他所想的截然不同。
草棚搭建的寺门简陋而破旧,与预想中相去甚远。寺院外没有华丽的围墙,只是用一排斜插的树枝做成的篱笆墙,勉强将寺庙与外面茂密的草木隔开。掉了漆的门匾上,依稀可见“灵隐寺”三个楷体大字,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显得沧桑而久远。
眼前的寺庙其实就是一处山野间破败的三进小院。李丹青失望之余,提起腰间的葫芦咕咚灌了几口,摇了摇头,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怅然。
寺门的木栅栏半开虚掩着,李丹青轻喊几声,却无人答应。他推开栅栏,步入寺内。外院是一块条石铺砌的空坝,左右都开垦出一片菜地,可见寺中僧人的清苦。穿过二门来到内院,只见寺院房舍呈“品”字形构造,中间主殿的外漆已脱了颜色,屋顶的瓦片也生了青苔,给人古老残败之感。
在院中一颗高大的榆树下,一位身着青布袈裟、浓眉大眼的方脸和尚正拿着扫帚打扫庭院。见有外人到访,和尚放下扫帚,颇有些意外。
“额弥陀福,请问施主到寒寺有何贵干?”和尚双手合十施礼道。
李丹青也学着和尚的样子,双手合十鞠了一躬,面色虔诚地答道:“大师有礼了,我叫李丹青,是中州人士。经师傅赵炳忠介绍,特来拜访赵炳和师傅。”
“哦?我堂哥介绍的?”和尚眉目中露出惊讶之色,“贫僧正是赵炳和,请问小施主这么远来找我,所为何事?”
“你就是赵炳和师叔,可找到你了。”李丹青闻言,惊喜万分,急忙从包袱里取出一封家信,递给赵炳和说道,“这就是师傅给你的信,你看完就知道了。”
赵炳和接过书信,仔细阅读后却面露难色。他侧身思索片刻,然后带着李丹青走向正房,嘴里交代说:“我带你去见慧明大师,向他说明情况。但能不能留在寺中,我不敢打包票,需得大师同意。”
大殿中间塑一尊释迦牟尼佛,左边是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琉璃光佛,右边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李丹青瞪了一对眼珠子只能好奇的看个稀奇,却叫不出名字。
释迦牟尼佛像下,一位老者正闭眼参禅打坐。赵炳和不便打扰,只得引着李丹青在一旁默声等候。一炷香后,老者功课做完,赵炳和俯身在慧明身边耳语片刻。老者缓缓抬头,眼光落在李丹青身上打量了一番。
李丹青见老者慈眉善目,虽已年过花甲,但却脸色红润,呼吸匀称,俯仰间可感超脱于世,目光炯炯,如能洞悉万物,与老者对视一眼后,便低头不敢直视。
片刻后,老者缓缓开口道:“贫僧已听慧远告知小施主来由,佛门本是清净地,小施主六根未尽、尘怨未了、身上杀伐气甚重,不便长留寒寺。”
老和尚说话文绉绉的,但最后几个字李丹青倒是听得真切。“不便长留寒寺”就是不愿收留自己,李丹青讪笑一声,不免一脸怅然,黯然失色。心想自己父母含冤离世,大仇未报,眼下又投靠无门,前路茫然,不觉悲从心来,眼眶红润。但是人家不收,也不可能强求,李丹青扭头抹掉眼泪,倔强的准备转身离去。
就在李丹青张口道别之际,只听慧明又开了口,缓缓说道:“听闻小施主身世悲苦,眼下已无去处,佛家以慈悲为怀,可暂且收纳施主在寺中打杂,但不剃度、不诵经、不参禅,不入佛门,施主意下如何?”
赵炳和听闻老和尚松口,连忙惊喜的示意道:“主持肯收留你了,你还不快道谢。”
李丹青只觉悲喜全在一瞬之间,刚才还暗自伤神,不知去处,现在却能留在寺中,顾不得擦掉惊喜的眼泪,连忙磕头跪谢。
寺院上下只有慧明、慧远两人,听赵炳和说前阵子还有位慧清师傅,后来还俗了。李丹青便暂住在慧清留下的床铺,和慧远同在西厢房。
自打李丹青住进寺院后,慧远就将寺院中的一应规矩对他做了叮嘱,也把原先由自己承担的琐事一并交给了他打理,主要负责挑水、砍柴、洗衣、做饭、扫地等寺中杂物。
李丹青出身贫寒,对于这样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他只求头上有片瓦遮身,因而毫无怨言的一人将院中杂务揽下。每天四更天起床,鸣钟三通后,慧远跟随慧明做早课礼佛诵经,李丹青便打扫院落、生火做饭。早饭后,慧远坐禅行香,李丹青则下山挑水打柴洗衣。午后,可得片刻休息,下午的时间也相对宽裕,慧远有时会带着李丹青一道打理菜园,修补屋舍,有时也能闲聊几句。
李丹青虽然厨艺不佳,但佛门的饮食本就清淡,对食物的要求也不高,一日两餐,只需将食物煮熟蒸热即可。两个师傅也不挑,他们常常就着一些腌制的咸菜和菜园里新鲜采摘的蔬菜,就可简单而满足的对付一顿。
李丹青三两日便熟悉适应了寺中的生活,也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手脚麻利、勤勉聪慧,将两位师傅的生活起居打理得井井有条。无论是清晨打扫庭院,还是午后的砍柴洗衣,他都做得有条不紊。
李丹青入寺后,赵炳忠终于可以当了甩手掌柜,免去了俗事,一心礼佛,心中自然欢喜。而老和尚慧明的脸色也渐渐有了些笑意,对这位新来的弟子颇为赞许。
一切又归于宁静,鸡鸣而起,日落而息。李丹青很满足眼前的生活,只是空闲时有些担心家中的弟妹,夜间常被噩梦惊醒,想起死去的爹娘,蒙在被窝里偷偷的落泪。母亲留下的十枚铜钱,那日为刺杀白世举买鞭炮用去九枚。剩下的一枚,他便用了红绳穿上挂在脖间,留作念想。